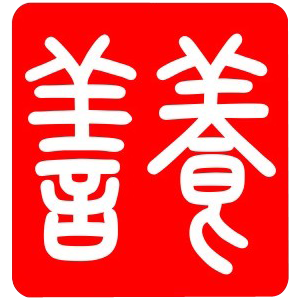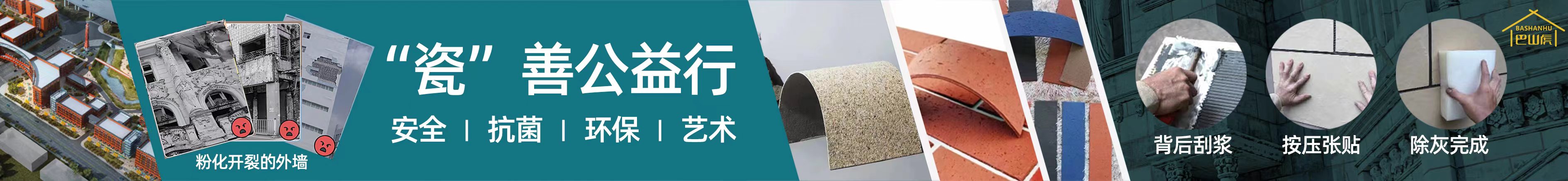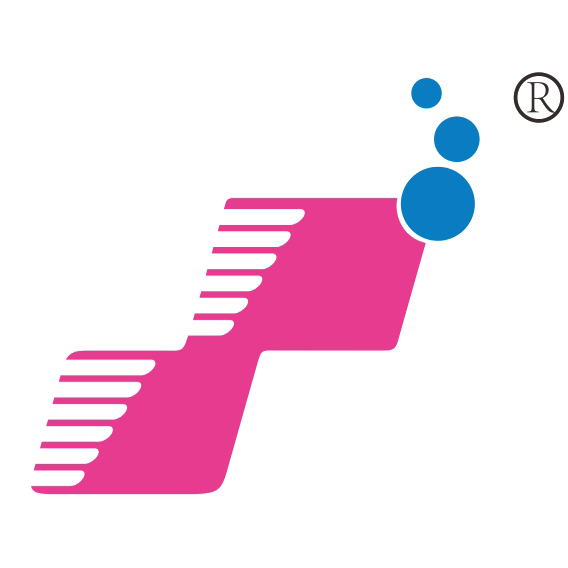《我爱你!》:“老年偶像剧”能让我们不畏衰老吗?
在大片当道、热度为王的今天,韩延执导的电影《我爱你!》从题材到阵容,无疑都并非端午档市场主流之选。这部由惠英红、倪大红、梁家辉、叶童全员老戏骨阵容担纲的作品,自上海电影节甫亮相便斩获无数眼泪。
《我爱你!》创下上映以来日票房稳居第二,仅次朱一龙、倪妮主演《消失的她》的不俗佳绩。
正如前作《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韩延探讨生死与爱情,不同点在于,“你可能会躲过疾病,死亡可能离你还很远。但衰老每个人都躲不过去,它日复一日地在发生”,这一次,浪漫故事的主角从光鲜亮丽的男女换成年龄总计逾250岁的演员们,爱侣间一句寻常告白都变得陌生,汹涌的火花也带着几分只是近黄昏的残酷。
代际悬殊下,贯穿银幕内外的审视眼光,又成为电影意犹未尽的弦外之音。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一场宣传造势的直播中,有年轻观众连线提出尖锐的观感:“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还没到那个年纪,看完片子后我感觉有些不适,我觉得人老了之后就别爱不爱了”,画面那头的主演之一、生于1960年的惠英红一怔,语带哽咽地回应,“对不起,没有让你看到你所想看的美女帅哥,看到几个老头老太太,我刚才也说了,我也老了,但我还是需要爱,每个人都需要爱”。
诗人痖弦形容晚年滋味,“我们老了,但没有老透,拨一拨火堆还有未燃部分,炉火微红,还可以支持一个寒夜”。常听长者将诸多衰退与疾病,归咎于“老了就是这样”挂在嘴边,心安理得的后辈又是否认真思考过,其实是哪样呢?只能这样了吗?炉火微红的他们,又需要怎样的爱?
撰文 | 一把青
爱得深沉,一体两面
《我爱你!》原著为韩国漫画,亦有2011年韩版电影珠玉在先,而正如中国版标题中的那刺目而热烈的惊叹号,韩国已经对老年生活景况题材探索得很远,不仅有传达“人生没有结束,我们还活着”的温情剧集《我亲爱的朋友们》,也有反映老年性交易、以65岁妓女为主角的破格电影《酒神小姐》。而在国产作品中,老年群体往往仍是主线之外、或为强化家庭冲突、或为突显礼孝仁义的工具人,出演主角的机会都屈指可数,更遑论谈情说爱。
《我爱你!》的人物关系并不复杂,丧妻多年的游乐园退休员工常为戒(倪大红饰),为了送孙子跟粤曲名旦学戏,结识了仇老师的贴身保姆、平时拾废品贴补家用的李慧如(惠英红饰)。朝夕相处间,理解了彼此生活的难处,误会涣然冰释,她发现他的铁汉柔情,他也被她的细腻与善良打动。
如果说韩版中送牛奶老头与收废品老太太的恋曲,是小城故事里的唯美韩式纯爱风,导演对中国版常与李情愫的刻画,则打破了一个所谓“黄昏恋”的刻板印象:过了激情洋溢的年龄,生活逐渐被柴米油盐与照顾陪伴淹没,似近还远的死亡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金风玉露一相逢,他们的爱意仍旧可以没有丝毫暮气。动物园的约会试探得欲说还休,开车捡瓶子则像个狂野的公路电影,深宵里的微信聊天彼此喜形于色又都带着些矜持,酒后闹起矛盾反手一巴掌也绝对没客气——在充满层次感的演绎下,“黄昏恋”未必总是缓慢慈祥的,爱情让人重新迸发出的滚烫得令人灼伤的生命力,年轻、灿烂得与年轻时无异。
至于另一对爱人,废品站的谢定山(梁家辉饰)与失智妻子赵欢欣(叶童饰),是少年夫妻老来伴的涓涓细流。叶童所饰演的阿欣,以最少的台词贡献着最神级的演技,呈现的远不止老年痴呆症混沌茫然的瞬间。复杂的神态变化如此鲜活立体,有纯真、有新奇、有依恋、有忧愁,更难得地说服观众,虽然是病人与被照顾者,她最重要的身份仍是被悉心保护着的妻子,值得被最大程度赋予快乐与尊严。无药可治的阿尔茨海默症,在情比金坚的爱意之下,都显得像是可以消融的难题。
谢与赵的一生相守,让人想起日本作家佐野洋子在晚年生活随笔集《无用的日子》(简体中文版译作《痛快的日子》)中,也曾坦然记述人生最后10年的胆怯与惶恐:乳癌转移、健忘严重到有痴呆风险,不会操作电脑手机,收到的电话越来越少,生活只剩下以床为圆心的50米活动半径,吃饭、睡觉、沉迷韩剧,衰老如同虎视眈眈的猛兽,看着同龄人,她也时常唏嘘,“大家曾经精彩而绚烂的生命都到哪里去了呢”。
有次电视播放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英国音乐家与妻子访遍名医而徒劳无功的纪录片,十年以来,男主角都只有七秒的记忆,因此,妻子反复问同样的问题,他也会回答,但七秒钟后就会忘记自己回答了什么,“不过不记得也挺好的吧,她的丈夫笑起来是那么开心,问他同样的问题,他不也总是会做出同样的回答,交流也不单单是靠语言,对人无微不至的关照,人也是能感受到的。沉默的日本人经常让人捉摸不透到底在想什么,但在少量言辞背后的千里沃野,不是隐藏着深厚的恻隐之心吗”,佐野洋子写道。
如果常与李一对,鼓足勇气说出“我爱你”三字,是要逾越内敛的东亚文化羞于启齿的心魔,谢与赵尽在不言中的恬淡日常,则是其一体之两面,融化在举手投足间的爱意,更需要庞大的信念感支撑,跨越顺境与逆境、疾病与健康的陪伴。有的爱情只有死亡可以隔断,有的爱情可以把死亡隔断。
浪漫包装,残酷现实
两对贫苦的爱人,在小世界中自得其乐,分享悲喜彼此支撑,苦难也变成甜蜜,但还是难以阻挡地走向迥异的结局:山哥在得知阿欣癌症末期后,与妻平静地在家中烧炭自尽,告别折磨,终于可以手牵手睡个安稳觉,换取永恒的平静;慧如在经历了山哥伉俪的身故,因为害怕再次承受失去爱人之苦,霎时间失去了拼命鼓起的勇气,而为戒还是难忍失落与思念,远走千里追爱,有情人终成眷属,展开诗情画意的田园余生。
生离亦或死别,固然没有孰是孰非。但主打“接地气”的电影行文至此,却暴露了其脱离现实的一面:真的能有那么美好吗?韩国原版中,另一对爱人的离世让女主角决定独自回家乡,选择把美好都封存在记忆里。当与男主角再相逢,他戴上了她送他的信物皮手套,骑着摩托车轰隆隆潇洒而来,画面一转,病房中,男主角在家属围绕下合上了眼睛,开放式的结局,是留白亦是点到即止的真相。为自己活一次本就不易,当人至暮年身体成为牢笼,在“只剩下以床为圆心的50米活动半径”的现实下则更是举步维艰,成全与放手,未尝不是将心比心。
更何况,不美好也无妨,甚至是另一重角度的真实。同样是老年爱情题材,与《我爱你!》形成镜像的,是提名金熊奖的英国电影《四十五周年》。凯特筹备45年结婚纪念日之际,丈夫杰夫突然收到来信,指50年前登山去世的前女友冰封的遗体已经找到,他沉湎于对旧爱的怀念,凯特则一夕之间陷入对45年婚姻的怀疑和自我身份的危机。那些看似相敬如宾的日夜,早逝的旧爱人“就像她一直站在房间里一样,影响了我们的所有决定,去哪里度假、看什么书、选择什么狗,听什么音乐”,经过反复的煎熬,纪念日派对上,众人艳羡的恩爱夫妻重新跳起订婚时的那支舞,电影戛然而止在凯特抽身离去时失望与苦涩、决绝与释怀交织的神情。当爱情的困扰发生在古稀之年,回旋的空间更小,选择的顾虑亦更多,种种无奈与颓丧,则暴露得更为彻底。
这显然是更进一步的探讨了,在《我爱你!》“老年偶像剧”式的包装下,就连房子、遗产、退休金等众所周知的考量,都仅以常为戒的几句醉后失言带过,为了填补这份主线爱情过于浪漫化的缺憾,导演有意添加两个家庭的内部戏码,加之人伦孝义的探讨。
当儿女纷纷步入中年,有的婚姻自顾不暇,有的一心鸡娃,有的汲汲名利,难得回家吃餐饭,也只是例行公事的尽孝,与老人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所以紧跟时尚、满口流行语、游戏玩得溜,都是常为戒的保护色。他被离经叛道的孙女点出是“讨好型人格”,仿佛不讨好这个时代,就会变成被遗忘的透明人,失去自我价值,连发微信、用手机这些社会人的基本技能都无所适从。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更加需要依偎取暖的情爱,因为在儿孙面前总是难掩孤独。
对此,导演以谢氏伉俪葬礼后,常从戒在宴席上怒挥麒麟鞭痛斥逆子的爽文式场面,给予了观众一个并不那么具体的回答。当麒麟鞭出现的场合,从广场舞晨练的公园移师到充斥小辈伪善言辞的酒楼,确实象征着老年人对话语权和主体性的再争夺。但是,“头三鞭,打的是恩将仇报白眼狼”“后三鞭,打的是没心没肝不孝子”,怒怨交织的悲鸣听起来难免像空洞的咒语,三言两语就让子女齐齐良心发现下跪认错,消解一辈子的误解与隔阂,显得宣泄有余而合理不足。就像常谢二人田园牧歌式的结局,一切轻易圆满得像个假象,反而衬托得前期的漫长铺垫、情绪的逐渐堆叠头重脚轻起来,而那些难以言说的不堪,才是导演与观众心照不宣的、暮年爱情的真相核心。
只能说,议题抛出易,抽丝剥茧难。毕竟在目前的社会语境下,抛出“人老了还需要爱吗”这样明知故问的问题,都会面临质疑的声音。也许借《我爱你!》,我们可以踏出探讨的第一步,就像早几年也曾是小众题材,如今已蔚然成风的女性主义作品一样,在一个个不完美的尝试中,挖掘更多老年人“做自己”的面向,让主创不必为年龄而道歉,打破缄默与偏见,不畏惧衰老,从不回避衰老做起。
撰文/一把青